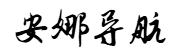二诡案异香
陆华庄的格局独具特色,进庄门就看到三座大堂,东西北各占一方,青砖红栏,装饰陈设各有千秋。三堂占地均等,谁也不比谁多出一寸,少上一厘。外人看了多赞气派,内人只道压抑非常,因为陆华庄三位堂主长年貌合神离,气氛恰如这三堂坐镇,针锋相对。
正中流影堂,堂主陆书云,是前庄主的长子,理所当然接任了庄主之位,继承了陆华庄的武学一脉,尤擅暗器与轻功。
右方翊锦堂,权掌财政,堂主陆书庸,陆远程次子。
左侧存岐堂,精擅毒理,亦通岐黄,堂主陆书瑛,陆远程小女。
陆华庄闻名于世的三样绝活恰好被前庄主均分给三个子女,一手造就了三足鼎立之势,让作为现庄主的陆书云着实辛苦。
偏偏此次闹鬼闹得恰到好处,人就横在翊锦堂后院,哪怕再偏个几步也可算作是墨阁的范围。但别说几步,就算要死人自己挪个几厘米也有点太强人所难了。
尸体旁边蹲着一个模样俊秀的人,是存岐堂的得意弟子柳笙,办完外务,一炷香前刚回到庄里。他一番查验,发现尸体脸色苍白,神情惊恐,像是受到惊吓,心口处插了一把匕首,刀身整个没入肉体,血流了一地。
柳笙认得此人,名戴全,年十七,江南徐安人氏,家中是做布匹生意的,前两日刚被三眼鬼婆招入翊锦堂。他起身理理衣襟,故意向身旁的人抛出话头:“巽师兄,你说好端端一个人,怎么就被鬼瞧上了?”
柳笙生性风趣,与陆宸是一路性子的人,偏就喜欢与司徒巽说笑。同屋同宿,低头不见抬头见,长年处下来,司徒巽竟然也习惯了,顶多是耳边一阵风,过去就算了。
“最后与他一起的人是谁?”他将所有人集合在院中,冷声质问。
角落里隐约有个身影哆嗦得特别厉害。
司徒巽缓缓向那人所在的方向逼近了两步,再问已有所指:“是谁?”
话音刚落,正哆嗦的那人双腿一软,膝盖生生地磕到石地上,看得在场的人都觉一疼。
谁都知道庄主待人宽厚,难办的是他的宝贝徒弟,行事毫无情面可言,前几日的明赫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每逢这种场面,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在心中将陆宸从头到尾骂个遍:你说,你才是庄主的亲儿子,怎么不争点气!大伙儿也少受些煎熬。
显然,司徒巽根本没听见众人内心的哀号,目光透着彻骨寒意:“名字?”
“崔玉,我叫崔玉,崔是姓崔的崔,玉是崔玉的那个崔,不,是玉器的那个器,不,不对,是玉器的玉?”
司徒巽挑眉:“你问我?”
“不不不,我,我是叫崔崔玉……”
柳笙看着心累,赶紧疏导:“师兄,不是衙门公堂,脸色还是缓缓较好,别死了一人,再吓昏一个。”说着,低头看向几乎吓瘫的人,“知道你叫崔玉,不必再纠结。师兄如何问,你便如何答,可好?”
都说陆华庄除了鬼神,大多是怪人,若说有谁可称作谦谦君子,定然是柳笙当仁不让。因此,崔玉跟见着救命稻草似的直扑过去:“柳师兄,你信我,我没有杀戴全,绝对没有,是鬼杀的。近两日,他的举动不太正常,肯定是犯了忌讳了!”
柳笙任他抱着腿,苦恼地道:“这话我可听不明白了,难道鬼也懂耍刀子?”
“我,哪知……可戴全确实招惹了不干净……”
“胡言乱语。”司徒巽打断他,“戴全因刀致死再分明不过,你妄想以鬼神动摇人心,不如去和阎王解释。”
崔玉顿时吓得涕泪横流。这让柳笙很为难,他倒不在乎向谁解释,只因一条腿还被紧紧抱着,那一脸鼻涕眼泪随时可能赖上自己,若将崔玉一脚踹开,又显得不近人情。
此时,翊锦堂正门传来骚动,一行人在夜色中匆匆而来,为首的正是庄主陆书云和两位堂主。在看到后院的惨状后,毫无例外地大吃一惊,只有存岐堂堂主陆书瑛戴着面具不甚明了。
陆书云面色凝重:“巽儿,怎么回事?”
司徒巽沉声道:“有人杀了戴全。”
陆书云话音一沉,再次确认:“有人杀了戴全?”
他的前两个字问得特别重,加之院中惶惶不安的气氛,司徒巽猜测,肯定是弟子又说了什么闹鬼的玄乎之言。他扫了一眼戴全,话语笃定:“恶意行凶,是人,非鬼。”
他指向翊锦堂通往后院的一个小门,从这个方向望去,门扉被隐在了矮树枝叶里。
当时的记忆非常清晰,他领着几名弟子于庄中例行检查,途中突然刮起大风,他巡查到翊锦堂时,远远地看见一名黑衣人迅速往弟子居所方向逃窜。他飞身追至后门处,便瞧见戴全躺在此地,血还在流,呼吸已停。事后,他搜过弟子房,并未寻到蛛丝马迹,且那时距离黑衣人太远,没有看清样貌。
柳笙总算找到借口,把腿抽回来,还好赶得及时,衣摆依旧飘扬。他谦和上前,将刚才所得情报一一汇报,末了又道:“庄主是否考虑尽快验尸?实际上弟子尚有一惑未解。”
陆书云神情闪烁了一下:“你先说无妨。”
柳笙沉吟片刻,道:“此地开阔,翊锦堂中又栽有桃花,所以巽师兄与众位师弟未能察觉。可弟子探查尸体时,隐约闻得一幽微香气,并非花香。”
香气?
众人疑惑,这年头鬼不仅懂得使刀子,还变文雅了?莫不是艳情小说里的狐鬼蛇妖一类?庄里有不少弟子都爱看,常压在被褥下。有几个胆大的凑上来仔细一闻,好像真有这么一股香味,挺迷惑人的。
漪涟想着陆宸常捣鼓香料,说不定知晓一二。转头发现他正眯眼盯着尸体瞧,神色凝重。
“果……果然是鬼,不然怎么尸体还会有香味?”
“是的,庄中闹鬼也不是第一次了。”众弟子议论纷纷。
陆书云见弟子们个个人心惶惶,一时又无法可解,以致愁容满面。倒是一直还未说话的陆书瑛开口道:“笙儿,这香味怪异,你且搜搜他身上有无疑点,也好让众弟子心安。”
柳笙的目光落向她,铜面具在人群里十分显眼。他迟疑了片刻,蹲下身,小心翼翼地检查起戴全,竟然真的在其腰间碰到了一样东西。他用绢布覆手将东西取出来,众人定睛一看,居然是个打制精美的小盒,香味无疑是从小盒里散发出的。
霎时,有几人变了脸色。
江南李主帐中香?
正是皇帝御赐的那一盒。
陆书云猛地回望:“宸儿,这是……”他私心顾及儿子,后半句压在喉咙里,没有问出来。
一干不知情者被这场景搞得茫然,眼珠子不停转动,发现几个说得上话的人物统统向陆宸看去。陆宸本人则是死死盯着精致香盒,露出撞鬼的表情。
陆书庸仗着眼小,用余光左右瞄了瞄,脑子里飞快地转出一个主意。他不说话,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身边的得力弟子使了个眼色,那弟子即刻会意:“陆宸,是你杀了戴全!”
他素来和陆宸不和,逮着机会是用吃奶的力气喊,当场掀起轩然大波。
数十道目光恍然回神,纷纷投向陆宸,既是诧异,又是迷惑。庄主的儿子,甚至是下一任庄主,为了什么了不得的原因要去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喽啰?
陆宸吼回去:“我杀他有什么好处?胡说八道!”
等在一边的汪楚濋当然不会袖手旁观,试图向陆书庸求助。
陆书庸眯着眼哼了一声,摆出为难样:“宸儿说得有理,无仇无怨,杀戴全作甚?你不许胡言,伤了庄中和气!”
“不是弟子挑拨,流影堂向来和我们翊锦堂不对头。陆宸摆了大师兄样,做老好人,暗地里还不是变着法子打压我们?”那名弟子愤愤不平,“前几日司徒巽关了明赫,大伙儿都知道。戴全这批新入弟子不大服气,抱怨了几句,说不准正是为了这事。”他对陆书庸道,“堂主,您可不能轻易算了。”
不等陆书庸说话,陆宸抢先道:“别说打压,近几日,我压根儿没碰见过戴全。”
那弟子道:“证据还落在人怀里,口说无凭。”
陆宸辩驳:“那盒东西我早丢了!”
那弟子道:“是丢了,可不就丢在戴全怀里!”
两人一时争得不可开交。
汪楚濋欲替陆宸说话,却被陆书庸不着痕迹地拦下来。他语重心长道:“宸儿啊,撇去三堂恩恩怨怨不说,二叔平时算待你不错,楚濋的心思,你肯定也明白。若当真为了这点小事动手,的确是不该啊。”
陆宸再次强调:“我没杀戴全。”
陆书云也道:“二弟,事情未查清楚,不要妄下定论。宸儿的心性我最清楚,他即使帮流影堂强出头,也绝不会动手杀同门弟子。”
“哎呀,瞧这话说的。”陆书庸蹙紧眉头,“流影堂还真有旁的心思?”
陆书云严肃反问:“为兄不仅分管一堂,更是一庄之主,自认平日处事绝无偏私。二弟,你是在指什么?”
又开始了!
弟子们不约而同地捏了把汗。
三堂本就是针锋相对的关系,一点星火便可燎原,何况是一个大活人栽在翊锦堂,陆书庸巴不得早一刻把这烫手山芋扔出去。结果陆宸自己撞上门,恐怕局势将会一边倒呀。
“一盒香而已,算不得确凿证据。”人群里忽然幽幽冒出一句话,众人一瞧,果不其然,是陆漪涟。她打量着戴全:“这盒香是被戴全贴身收着的,若是凶手无心遗落,该掉在一旁,还能故意揣到死人怀里去?”
陆书庸道:“话差了。”他用那双小眼瞟了瞟,“单就案情说,戴全是正面中刀,很有可能案发当时凶手正与之说话。说不定是谈话中戴全收起了那盒香,凶手趁其不备,捅了一刀呢?或是戴全中刀后还存了一口气,将凶手遗落的东西收进怀里保留罪证也未可知。”
漪涟不认同:“柳师兄方才瞧了现场,证实他是当场毙命,巽师兄赶得及时,也没发现戴全为了保留罪证多喘一口气。若按二叔说的第一点,戴全是事先得到了那盒香收了起来,却没有证据证明他拿到香以后马上中刀,这样一来,不是谁都有行凶的可能了?”
众人觉得有理。
“若说可疑之处,恐怕不止那盒香。”漪涟又挑起一个头。
陆书云问:“阿涟,你瞧着哪里不对?”
漪涟问柳笙:“柳师兄以为凶器如何?”
柳笙道:“是把新匕首,庄中常见,并无特别之处。”
漪涟道:“庄里领用物品都有很详细的记录,多亏二叔行事谨慎。匕首不是一天一换,数量也不多,只要照着记录详细对一对,便可以知道这把凶器的出处。不过如此新的匕首多半来自仓库,而仓库又属翊锦堂管辖,不知二叔对这把凶器有没有印象?”
众人惊讶,是逆袭呀!转着转着,又转到翊锦堂来了。
陆书庸脸部的肉一抽,眼眯得更小了:“这个……前几日我是从仓库提了一批出来,没来得及发放各堂,也许是弟子看管不力,丢了。”
“是丢了,可不就丢在戴全心口了?”漪涟原封不动地把话还回去,并且恳切表示,“是人,总有大意的时候,我哥会丢东西,您当然也能丢。”
陆书庸闻言不爽,可他一个老到之人,绝不是好欺负的,阴阳怪气道:“翊锦堂再大意,总不见得拿自家的匕首杀自己弟子,还光明正大地扔在自家地盘上。可见此事摆明了是有小人陷害。但他丢下流影堂的香又是为何呀?”
的确,即便同样有嫌疑,两者的分量仍旧不可相比,毕竟三堂之间还有恩恩怨怨摆在前头。这个道理弟子们懂,陆书云更加明白。
他侧目片刻,转身正对陆书庸:“庄中事分三堂,只因我兄妹三人各有所长,利于我庄发扬光大。可无论是哪堂弟子,皆是陆华庄的弟子!”他微怒质问,“如今戴全出了意外,你不计较查明真相,不计较料理他后事,反而急于分清三堂是非。二弟,你是本末倒置,还是另有缘由啊?”
强势的态度居然令陆书庸有点心虚,他古怪地移开视线:“我不过就是一问,长兄未免言重了。”
“但愿如此。”陆书云沉声道,“证据确凿之前,二弟慎言!”
众人不禁感叹,真是一出好戏!
虽说三堂平日里气氛压抑,但掐起来可比压床板的艳情小说精彩多了。
陆书云感觉气氛越来越糟,赶紧下令道:“三妹,你且将尸体抬去存岐堂验尸,久拖不宜。巽儿,你从三堂里分别增派人手,部署好,将名单交给为师验看,另外再将崔玉移居偏院,着人看守。”
众弟子奉命行动。
不料尸体刚抬上担架,一张纸条晃悠悠地落到地上,隐约沾了血迹。
漪涟眼明手快,不等众人反应过来,首先冲上去拿过纸条。她凑近灯笼凝神看,纸条角落颜色发黑,略粘手,确实是血迹。还好,上面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大概还辨认得清楚:“太皞治夏?”
众人一听,又愣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?怪事年年有,陆华庄特别多!
太皞?他老人家不是东方天帝吗?按理说,要管也是管春天的事,什么时候跑去隔壁抢炎帝的活儿了?呵,这年头,鬼跟神都不走寻常路。
汪楚濋蒙得尤其厉害,恰到好处地蹦出一句:“爹爹,是不是你常瞧的那句?”
陆书庸瞬间脸色发青。可想而知,汪楚濋这话实在蠢极了。只是陆书云的表现亦十分反常,他对这纸条视若无睹,兀自领着陆书庸和陆书瑛二人径直离开,丢下了一个烂摊子给司徒巽收拾。
唉,多少弟子慕名拜入陆华庄门下,求的不是好吃好喝就是出人头地,总有一点欲求一腔抱负。谁知栽到了鬼窟窿里,平日被吓吓倒也忍了,怎么还真出了人命?眼下别说啥抱负,恨不能一头扎进老家的被窝里才是真的。
漪涟思来想去,帐中香的来龙去脉是关键,岂料司徒巽故意打断她与陆宸搭话,厉声道:“把大师兄押入后院禁足,再待庄主发落。”
全场愣住,呆然不动。
啥?押……陆宸?
众弟子傻眼:可……可大师兄他……他……他是庄主的亲儿子呀,说关就关?胆子忒大了。
漪涟愤愤不平地强调:“现在没有切实证据!”
司徒巽低眉看她,闷声道:“正因没有切实证据,才须禁足。”
按理来说,司徒巽的决策是不错,但漪涟担心陆宸心气高,受不了冤屈。结果一个眼神瞄过去,视线恰好撞上了陆宸的视线,他左眼跟犯病似的挤弄,看得漪涟十分嫌弃,心里说:你打暗示,怎么跟中邪似的?
瞧瞧人家柳笙,闲庭信步而来,迎着桃树落花轻摇折扇,端的是翩然风貌。忽然巧劲一收,折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敲在漪涟小臂上。
漪涟咒骂:“兄弟,你好歹轻点!”
她明白司徒巽是有意在护陆宸,免得身份尴尬,更容易招人话柄。大概是出于此心,才故意打断她与陆宸接触的机会,否则她会同样沾了嫌疑。
可柳笙的戏码改得飞快:“巽师兄,禁足之事是否先问过庄主?不论怎么说,陆宸都是大师兄,你我身为师弟,贸然处置总归不妥当。”
漪涟瞪过去,这假惺惺的又是演哪出?
司徒巽亦看了他一眼:“不必。带走。”
他的决心毫无动摇,众目睽睽下,雷厉风行地把陆华庄的大师兄给逮进了后院。众弟子在感叹世事无常之余,也服了司徒巽,真是谁都敢下手!他们心中有数,往后若是狭路相逢,只要没栽到跟前,有腿能跑的绝不逗留片刻。
柳笙事后表示,大师兄关是必须关,声势也不能落下。司徒巽当场做得越绝,陆宸往后遭的罪就越少。
“只是苦了巽师兄做恶人。”他摇着扇如此说。
弟子居是独门独院,除了陆宸,所有弟子集体夜宿于此。
三堂关系不和睦,堂下弟子亦是剑拔弩张,为着芝麻大的事常常吵得鸡飞狗跳,上房揭瓦。总结起来,就是大户人家那几房姨太太的关系。
住宿上理所当然分开安排,两间屋子例外。
一间集庄中大成,住了流影堂司徒巽和存岐堂柳笙。
柳笙是出了名的好脾气,说话似青柳拂水,加之风貌俊雅,与谁都合得来。主要是他主动担下了与司徒巽合宿的重任,弟子们直夸他觉悟高。也只有柳笙无惧罗刹鬼的威名,得了兴致还总喜欢调侃两句。说来真奇怪,司徒巽偏就拿他没办法,瞪眼无用,干脆绕道走。
庄里有这能耐的统共三人:柳笙、陆宸、陆漪涟。
其余弟子大多六人宿一屋。戴全和崔玉是被分剩下的,两人一屋,也是例外。眼下,戴全停尸存岐堂,崔玉被锁入后院,只剩一间空屋。
天亮后,司徒巽与柳笙奉庄主之令搜查屋子,看看是否留有线索。
两人进屋时,屋子还保留着戴全离开时的模样:被子摊在床上,掀开了一角,粟米壳枕头上还有躺过的压痕。司徒巽发现枕头旁边落了一个木人偶,拿起端详。
柳笙查崔玉的床榻,被褥整齐地叠在床头,回首瞧见司徒巽手中的东西,帮着解释:“那是伏羲像。戴全是徐安人,信奉伏羲。”
司徒巽垂目多看了两眼:“神像随手遗落,难以表诚心。”
柳笙用扇子轻敲床头矮柜:“之前我来过戴全的屋子,见他是将伏羲像放置在矮柜上的,想必是无心撞倒了。”
司徒巽扫了一眼矮柜,又打量了未整理的床榻:“昨夜他是匆忙离去,一定事出有因。”他将神像放回矮柜上,打开柜门,里面除了几套常服外,还放了一些冥币。
“清明之日,戴全有心了。”柳笙道。
司徒巽粗略一翻:“数量很少,像是剩下的。”
柳笙疑惑:“这便怪了,入庄一月,没见戴全烧过冥币。而且烧冥币怎么会剩下?”亘城比较讲究玄事,院里有个小的空祠堂,是专为弟子们准备的,免得到处烧冥币冲了哪路鬼神。
司徒巽将众弟子找来盘问,所有人都摇头说不知。
“戴全性子内向,忌讳又多,那尊伏羲像,他一日要擦三次。”有个存岐堂弟子道,“我听老家阿婆说,烧冥币好像有很多讲究,讲究时辰,讲究方位,戴全指不定懂这些。他要偷偷挑个地方祭拜,我们哪里会知道?”
司徒巽问:“昨晚你们可看到他离开弟子居?”
弟子道:“风刮得呼呼响,很多人起床关窗时都看见戴全跑出去,一溜烟没了影子。”
柳笙问:“可曾看见崔玉?”
弟子回答:“看见了,跟在戴全身后追了几步,不过很快又跑了回来。”
大略盘问完一遍之后,司徒巽和柳笙再次来到了翊锦堂后院。戴全的尸体被抬走了,地上还剩一摊血迹没清理干净。
柳笙试着重演昨夜情景,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:“问题出在戴全身上,他为什么在大风之时跑来翊锦堂?而且十分急迫,以致翻倒了神像都没来得及扶正?虔诚之徒,万不该有此疏忽。”
司徒巽道:“定与大风有关。”
柳笙道:“戴全乃徐安人,信奉伏羲。伏羲便是太皞,不知和太皞治夏有没有联系。”
司徒巽摇头:“字条之事,还请师弟代为查证。”
柳笙摇扇:“自然。”
两人分头行事前,司徒巽的一番张望招来柳笙挖苦:“不必看了,涟师妹最耐不住性子,要来早来了。”
“她人呢?”戴全的案子必查弟子居,一路走来,竟没看见她的身影。
“阿涟师妹下山去了亘城。”
司徒巽意外:“进城做什么?”
柳笙吊了他好一阵胃口,方说道:“今早我前脚刚回存岐堂,师妹后脚就到,硬是缠着要大师兄的帐中香。幸好我与验香的泉师弟有些交情,替师妹舀了一小勺。此时入城,大概是为帐中香而去。”
司徒巽担忧:“你怎么不懂劝着?”
柳笙反笑:“巽师兄,您都劝不住,怎能为难我?”话音落下,见人满脸愁容,他隐去笑容试探道,“你外出好几日,回来也不见你俩说过话,是不是师妹为了那夏姬气你了?”
夏姬就是永隆帝的夏贵妃,前段时日同皇帝出游一起来了陆华庄。
不愧为大兴第一美人,当真漂亮,骨子里都透着妖媚劲。庄中弟子为了一睹芳容,纷纷往门前挤着偷瞧,那时真没害怕惹怒皇帝。都说司徒巽不近人情,冷面无心,谁料也抵不住美人诱惑,接连三日魂不守舍,弄得全庄流言纷飞。
男人贪图美色,本性使然,原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,主要是前头摆了个陆漪涟!
司徒巽的心思,全庄上下都明白,连陆书云都做好了女儿嫁徒弟的准备,喜上加喜。为此,明赫之流心底很有怨气,暗地里指着司徒巽骂,说他是为陆华庄的权势倒插门。
不管是不是倒插门,作为陆家准女婿,对其他女人魂不守舍总是不对!
近两日,总觉得陆漪涟与之说话甚少,不知是不是为了这事。
司徒巽蹙眉道:“无事,改日我会与她解释。”